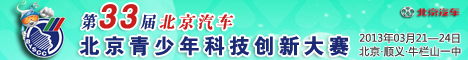芋(Colocasia esculenta),在我的家乡基本是与番薯齐名的,是很重要的粗粮之一。小时候,家里每年都会种上很多芋,芋头收获以后就存在家中,日常就与稻米等一块食用,或直接煮来吃,或和米饭一起煮饭或粥,还可以用来做汤等等。我还是很喜欢芋头的。
 
芋在外表上最引人注目的自然是它那堪与荷叶媲美的大叶子,只不过是卵圆形的,一端还有个小缺口。这种大叶子表面具有一层特殊的防水层,怎么也弄不湿,水珠在上面只会滚来滚去,晶莹透亮。小时候上学的时候常忘记带雨伞,南方又经常多雨,如果路边正好长有芋叶,我便会摘上一片顶在头上,这种天然的斗笠对于小雨还是蛮管用的。芋的大叶子也不光独具外表,还有其它实际的用处。芋的肥大叶柄撕去表面的一层薄膜后,切成小段,加上佐料,炖完后也是一道很不错的菜肴。多年以后,我在云南东南部便在街上见有出售这种芋头叶柄的,想必也是用来做菜吃的。不过,这道菜在我老家只是偶尔调配来品尝而已,更多的时候是将芋的整个大叶子直接剁碎煮熟后用来喂猪,这几乎也是我家养猪的主要饲料之一。

比起吃芋叶子,我更热衷于烤芋头。我的烤芋头方法和如今街上常见的煤炉烤红薯的方法不同,而是用一种我和一位小伙伴独创的方法来烤。烤东西自然需要燃料,在老家出门便是野外,柴火燃料是随手掂来的,本是不用费心的。但烤芋头还是有所讲究的,秸秆杂草等一烧就光的燃料是不适合的,大块的木材也是不舍得使用的,因此我用的更多是竹子,反正家门口便是一片竹林,还有很多篱笆也都是用竹子编成的。劈开的竹条还有一个好处,形状都是长条形的,大小粗细也很一致。利用这些竹条,横两条竖两条,搭成一个四方形,周而复始,到一定高度后再铺上一层竹条,接着再搭上面一层,就这样如玩积木般搭建出一座小型的四方塔,而要烤的芋头便放置在这座塔的各个层里面。这个塔修剪完工后并不是用来看的,而是马上从下面点火,这种四面通透的塔很容易点着,一会儿便烧光了,而里面放置的芋头便会烧得焦黑,埋在了炭火之中。点完火后,我也不再多看,而是等到炭火彻底熄灭、化为灰烬的时候,再用棍子从灰烬中扒出基本已经熟透的芋头。这样烤出来的芋头烟火味十足,吃着也是格外的香。当然这种方法也适用于烤红薯,那也是我小时很热衷的事情。

芋头的另一项重要功能便是制作芋包了,这是老家七夕与中秋的重要习俗。每年到了七夕或中秋,家家户户都会选一些大个的母芋(一般为白芋,这个品种的老芋头一般不能直接煮来吃),磨成芋泥,再和米浆(用生米加水磨成的)一起混合后,即是制成芋包的主要原料,一般还会制造各种菜馅包在芋包里面,最后再蒸一下,芋包将做成了。小时候家里每年七夕或中秋都会蒸上很多的芋包,常常可以吃上不止一星期。如今已经有10多年没有在这两个节日回过老家了,家乡芋包的滋味早已经淡忘。不过,厦门、泉州等城市还是有芋包这种小吃在卖的,可惜我也没有吃过。

家乡的芋头品种很多,这点我记忆尤深,起码我吃过五个品种以上的芋头,不同品种之间的差别还是很大的。其中,最好吃的大概便是槟榔芋了,这种芋头的母芋是主要的食用部位,熟后质地很面,香味也很浓,也名为香芋;红芋和白芋也很常见,这两个品种的母芋较大,但不易煮烂而很少被人直接食用,一般是将其捣烂制成上面所说的芋包,而其分蘖形成小的子芋,才是主要的食用部位;九头芋是形状较为奇特的一种芋头,母芋与子芋丛生并连成1体,大小相当,不能分辨,味道则较淡;此外,我还吃过1个不知准确名称的品种,其芋头呈长圆柱形,有时甚至能长达1米,老家称其为“竹芋”,这种芋头肉质也是面的,味道也淡;此外,我还吃过1回一种极粘的芋头,不过这种芋头似乎很是稀有,对其了解不多。

关于芋花,由于家乡种植的芋很少开花,记忆中仅是偶尔见过,印象不深。倒是在云南的时候见到有人卖过,原来这种花也是可以吃的,不过我从来没有吃过。芋花也是典型的佛焰花序,佛焰苞下部较短,紫红色,上部较长,黄色,里面是个肉穗花序。此外,没有什么特别之处。


|